土 殇
土 殇
C0709 陆遥
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,但是,它永远都摆脱不了灵魂的桎梏,只是更用力地印下悲凉。
——题记
拥抱涅磐的痛苦
我想,我再也没有脸面去栗子树旁,因为,下面躺着一具瘦小、痛苦的心情骸。
1998年,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悲伤。那年,家里的羊被野豺咬死,家里的鸡被人毒死,连黄牛都被人拽掉尾巴……家里的牲口一一惨遭毒手。天灾,人祸,连一只小狗,一只那么可怜的小狗,也未能幸免……
春天,明媚,父亲从乡里买来一条小狗,说是家里容易丢东西,养条狗看家。
父亲怀里的小狗,眼睛很澄澈。我伸出一只手,摸摸它的头,它温驯地闭上眼睛。
这只花色皮毛的小狗有了一个名字——麻犬。
麻犬刚到家里,我就用竹框和破棉絮给它赶了个窝,外边一圈还细细的围上稻草,窝里软得像席梦思,很暖和,窝很大,我就和麻犬一起蹲在里边。我读着语文书里的《乌鸦喝水》:一只乌鸦口渴了,它找到了一瓶水,可瓶口太小了……读完之后,我就拍着它的脑袋问:“小麻犬,你会不会也用石子把水填出来呢?”
二姐特别疼麻犬,每个星期读书回家,都要来看它,长大些了没有,窝有没有湿,有没有生病,如果有,她一定要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会放下书包……
平常的时候,二姐就坐在门槛上,一边看书,一边看麻犬在那里嬉皮。有时,麻犬顽皮过头了,去逗蜜蜂,被蜇了,痛得嗷嗷直叫,在地上打滚。二姐自然最着急,把书一扔就抱起麻犬看,再到菜园里砍魔芋杆子滴汁,烧针挑毒。这时,麻犬就会耷拉着半边肿脸老老实实趴在地上,我想,那时候的麻犬,是最快乐的。
夏天,麻犬才长到十多斤,在村子里是最瘦的,也许是家里条件不好,它只能吃剩饭喝洗锅水。可俗话说得好,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。村子里走失过许多狗,可麻犬从没丢过,它从不离家半步,每天,麻犬都去晒太阳,有生人来就吼。真的,如果狗的职业就是看家,麻犬就是最负责的工作者。
蓦然回首,是一片无尽泪痕
一天,杨老师告诉我们,不要去接触猫啊狗的,一是不卫生;二是那阵子流行“五号病”,乡里瘟了好多动物,怕传染给人。瘦瘦小小的麻犬自然是不知道这些,它仍然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快乐着,无忧无虑。
瘟病来了,村子里死了一条狗,弄得人心惶惶。
那个早晨,橘色的阳光穿过松枝,照在厨房前的弄堂上,二姐背着书包,站在前边,依依不舍地摸着麻犬。麻犬摇着尾巴,舔着她的手。二姐对父亲说:“爸,现在村里瘟狗,你可别放麻犬出去啊。”父亲嗯了一声,两个絮絮叨叨地说了几句,她才追着大姐的背影离去。
晚上,我去厨房,发现麻犬的饭盆里的饭还在,它瘪扁着卷缩在窝里,我唤它,它头抬了一下,尾巴摇摇又不动了,我以为他嫌今天的饭太干,于是倒了点菜汤,送到它面前,它舔了几粒,还是没有吃。
麻犬怎么了?
我叫来了父亲,他抬起麻犬的下巴,把它的眼皮拉开看,里边血红血红的,父亲不禁叫道:“啊呀!五号病!”然后赶紧把我推搡开,端起狗窝就往外走,我急了!它还没吃饭呢!它还没吃饭呢!
狗窝被放在吊脚楼下,父亲不准我去逗狗了,我把麻犬的东西都拿了出去,放在狗窝旁的木屑堆上,伤心地对它说道:“麻犬啊!我不能和你玩了,你快点好起来啊!二姐还没回来呢!”
深夜里,不时传来的狗的呜咽声,是麻犬吗?它冷吗?它饿吗?它伤心吗?
我不知道。
第二天,我在楼上捡从屋顶掉下来的碎瓦片,听到吊脚楼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我放下东西,飞快地跑下去,看,是麻犬,它痛苦地在地上挣扎,嘴里吐着白沫。我还没见过狗这样子,吓得不知所措,只好拎着它脖子后面的皮把它弄回窝里,头也不敢回地跑了。
“看来它内脏开始烂了。”父亲吸了口烟,他何尝不着急呢?
一只大狗匆匆走过,麻犬都要叫上好半天,偶尔有只狗停下来嗅一嗅它,它就艰难地爬起来,睁着一双混浊的红眼不住摇尾巴,但是,这只嘴里散发腐臭味的小病狗,谁会为它停留?
第三天,麻犬快饿得不行了,可它又什么都不吃,放在旁边的汤也给弄翻了,浑身粘乎乎的,全是土灰和木屑,已经失去了理智。五号病,学名就是急性热病,分春瘟、暑瘟、伏瘟三种,麻犬就是暑瘟了。五号病最初症状就是发烧,吃不下东西,再就是神志不清等等,看来,麻犬真的没救了,连内脏都坏了,可对这只才四个月大的小狗来说,这个死刑,判得太残忍。
能够安宁一会的时候,麻犬就要去晒太阳,走得摇摇晃晃,往有太阳的地方挪,太阳下山,就艰难地爬回来,一看到这场面,我鼻子就酸酸的。
正埋头看书的当儿,一声悚人的惨叫传来。
猛一抬头,是邻居家的大公牛,嘴里正嚼着杜桐叶子,而脚下,是麻犬。
麻犬的四肢无力地挣扎着,我一把抓起旁边赶鸡的长竿子啪地砸在牛身上,捡石头打它的头,它慌忙逃跑了。
麻犬肚子上留下了一个半月形凹痕,连脊骨都断了,浑身抽畜着,惨不忍睹。
我看着它向吊脚楼蠕着,留下一串血迹。
它叫了很久。
埋葬了一丝希望,忏悔已无用
第四天,那是我一辈子都要忏悔的痛苦的一天。
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,年少无知……
一位村人从屋前路过,他家才瘟了狗,看见麻犬,他马上叫我爸:“老国,你家这狗也瘟了?”我父亲嗯了一声。他又说:“还不快埋了,不然这四边的狗啊什么的东西都要瘟的!我刚瘟了一只狗呢,现在又死鸡了。”父亲嘴里的烟屁股掉了下来。
那人接下来说的话我都没听了,我就蹲在石板路上想着麻犬,怎么办呢?
小伙伴过来玩,我就跟他说,他就说去看麻犬怎么样了,然后再问问我爸。
麻犬早就半死不活了,奄奄一息地躺在狗窝里。我问父亲,他半晌不吭声,好一会儿才说:“随你吧!”
不一会儿,我和小伙伴,一人提锄头,一人提狗,到北边的栗子树下找了个地方。
当麻犬那皮包骨头的身子放进那又湿又冷的土坑时,它回光返照似地大叫起来,我吓了一跳,忙要把它弄出来。可它又踢又咬的,身上还那么恶臭,我们就是不敢伸手。
小伙伴往它身上堆土时,它叫得更响了。
直到土淹没了麻犬,被拍得严严实实时,我才回过神来,一下坐到地上大嚎起来。后来,我给它立了个牌子,写着“麻犬之墓”。就这样,还是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,活埋了一个充满希冀的生命,我没有给它离开母亲后的安慰,更没有在它求助的哀声中留它见二姐最后一面……
懵懂,是否也是一种悲哀
麻犬死后的第二天,二姐她们读书回来。
二姐吹着口哨,急切地寻找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。
“爸,麻犬呢?”
“弟弟,你是不是又把麻犬藏到柴垛里去了?快把他放出来吧!别逗了。”
“麻犬!麻犬?”
我默默地把二姐拉到了栗子树下,看着那个土包,看着土包上的牌子,她怔往了。
过了半晌,二姐终于开口:“它……死了?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瘟死的吗?”
迟疑了一下,我咬牙点了点头。
好一会儿,我回头看了看,才发现二姐手里紧紧攥着一包狗食,眼泪流了她一脸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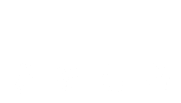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